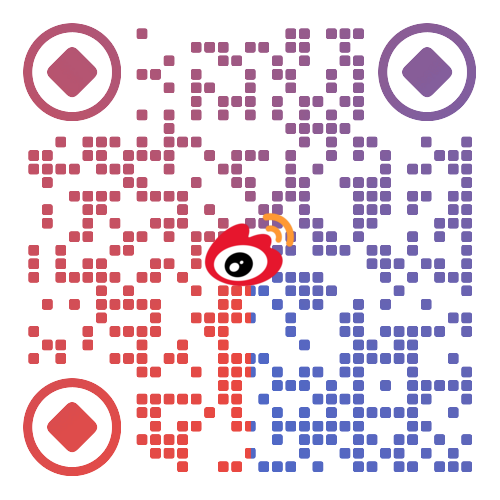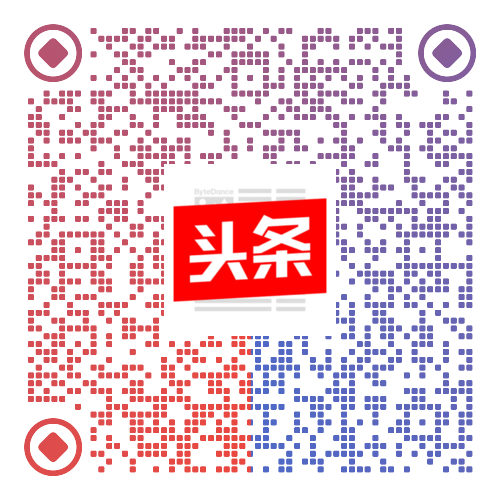我去见山
家乡在扬子江边,是江南水乡。平日里,举目所见,唯有河湖、圩田、村庄和不远处的低矮丘陵。山,是远处的一抹蓝黛之色,或深或浅,或隐或现。有时雾缠绕在山腰,有时白云飘浮在山巅,有时山隐在雾中,都是可远观、可想象的风景。天气晴好时,能望见远山的青绿。只此一瞥,也只此一片青绿,便留下了早年时我对于山的一种想象:山中有什么呢?或可知,或不可知,都是我想知道的。如此想来,我一直是迷恋山的。
有一年,跟父亲上街卖菜。大半夜起来,挑着两个菜篮,篮子里装了二三十斤菜,跟在父亲身后,赶十几公里的夜路,到市里的菜市场时,人已经累得不行。菜市场在一处铁道边,沿路多是和我们一样从乡下来卖菜的人。我们赶到时,天还没亮,路灯的光昏黄,只能照亮灯下数米的范围。我们放下菜担,找个空处停好,等着清早来买菜的市民。此时,晨光从东边亮起,渐渐能看清周边建筑的轮廓,多是红砖黑瓦的平房,间或可见几栋灰扑扑的楼房。及至太阳升起来时,才发现铁路边的露天菜市场就在山脚下,抬头便是山。此刻,在家乡常常远望的那座山,离我如此之近,那样高大。而此时,那座山之于我,既有陌生的亲近感,又有真切的压迫感。想不到自己第一次见山,竟是在一个不知情的清晨,如此突然而又突兀。
第一次出远门,是去徽州。一个少年,突然要去远方独自生活,心里既有憧憬,也有些许忐忑不安。和父亲一同坐长途汽车时,我选择了坐在窗边的位置。我望着窗外,不时回望,也不时远望。回望并不熟悉的离乡路,远望尚不可知的远方。家乡多平原,徽州多山。一路南行,也是一路向山而行。山不知我,我自去见山,有一种无知者的豪迈。一路见山,也一路撞进一座又一座山的怀抱里。我从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,见过这么多的山。群山连绵,过了一座山,迎面又是一座、数座;身后是山,山外还是山。我喜欢车行山间那种起起伏伏的颠簸感,车和人如浮于山间,又似陷入大山的某一层皱褶里。我们在大山里前行,不知是要窥视大山的某一层肌理,还是要拆分大山的某种结构。车行山中,山接纳了我们,却不让我们窥探它更多的秘密。我去见山,见了许多山,依然不知山、不识山。山是难识难懂的。
此去经年,我已非当时那个少年。想想,自己这些年见过的山,已经难以一一数过来了。见的山多了,便知山与山的不同,也晓山与山的几多相似。有段时间,见到一座新的山已经不再有多少惊奇了,可还是想去见山。过些日子没有见识一座新山或是未到山中去走走,便想去,这是另一种痴迷吧。我去见山,是一种心结。我喜欢住在举目可见山的地方,可以一眼瞥见远处的山,知道山不远我,心里就安稳了。周末,悠然地坐在自家的阳台上,观山不语,读诗不言,只有阳光在我与山之间,在书页与书页之间飞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