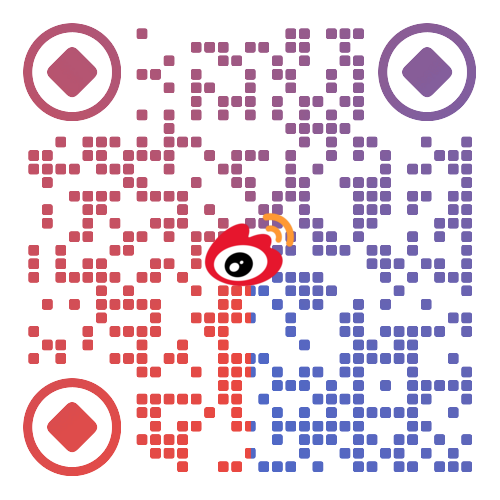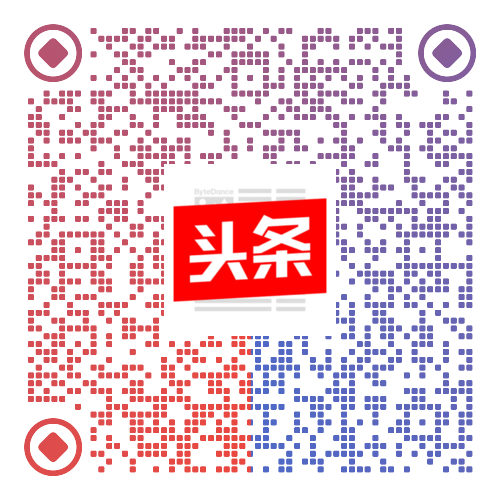足尖上的星芒
母亲并非舞者,她的步履总带着生活踏实的重量,对舞蹈的天地全然陌生。然而11年的光阴里,我足尖下的每一寸道路,却都无声铺展于她凝望的目光中。
幼年偶然路过少年宫,恰逢一群身着白纱裙的女孩在练习旋转。她们身姿轻盈如蝶,足尖点地,薄纱裙摆散开成了一圈圈完美的涟漪,仿佛踩着无形清风的旋律。玻璃窗外,我的目光被那纯粹的美钉住,心弦被无形之手拨动着。母亲察觉到我的神往后,那日午后,她牵着我的手踏入了少年宫舞蹈班的大门。
初学舞蹈,压腿时我疼得龇牙咧嘴,母亲便依着老师教的法子,用自己温热的手掌按住我的膝盖。她的动作生疏而迟疑,生怕多用一分力便折损了我稚嫩的筋骨。我额上沁出密密的汗珠,她为我擦汗的手竟微微发颤,仿佛那痛楚也丝丝缕缕渗入了她的掌心。那简陋的练功房角落,从此成了母亲固定的守望之地。她目光所及,便是我幼小心灵中风雨不动的灯塔。
后来,我的舞技渐长,投入愈深。11载春秋流转,练功房把杆上的漆色,也在我的汗水浸润下斑驳剥落。多少次旋转后头晕目眩跌倒在地,脚踝肿胀得几乎穿不进舞鞋,母亲总是无声地蹲下身来,替我缓缓按摩。她布满生活痕迹的手,如同剥落的树皮,动作却轻柔地如抚平一片羽毛,仿佛要将所有难言的痛楚悄悄揉散。
前年深冬参加关键比赛前夕,窗外雨雪交加、寒气砭骨。我紧张得食不下咽,母亲默默出了门。许久,她裹挟一身寒气回来,怀里紧搂着一个纸袋,里面是一双崭新的缎面舞鞋——鞋尖已缀好了比赛要求的特殊软垫。她的裤脚湿淋淋的,鞋底沾满泥泞,冻红的手笨拙地拂去鞋盒上的水珠。原来她冒雨寻遍了大半个城。她递过鞋时,只低声说:“试试合脚不?”——那朴素言语的重量,瞬间压弯了我酸涩的眼睫。
真正站上赛台那日,追光炽热。我昂首舒臂,仿佛11年的晨昏苦练都凝聚于此刻的腾跃。当最后一个音符戛然而止,台下掌声腾起。我望向观众席,母亲正悄悄用手指抹去眼角的光亮。那一刻我才彻悟,母亲虽从未读懂过舞步的章法,却以整个生命读懂了女儿对星空的仰望。
原来人间最动人的托举,并非聚光灯下那轻盈一跃,而是母亲那双从未沾染过镁粉的手,在尘世烟火里,无言地为你托起整个天空的重量——纵然她步履笨拙,不懂旋转的韵律,却懂得如何稳稳接住你每一次飞翔后可能的下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