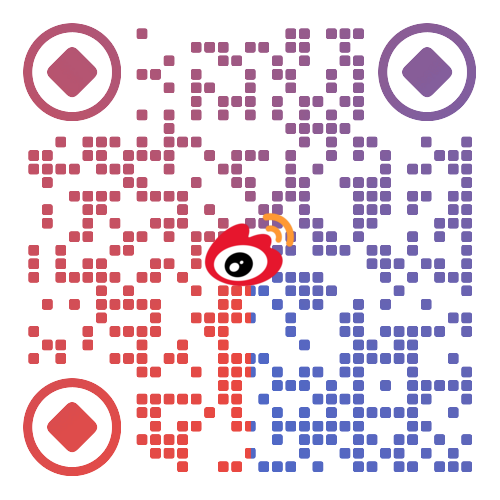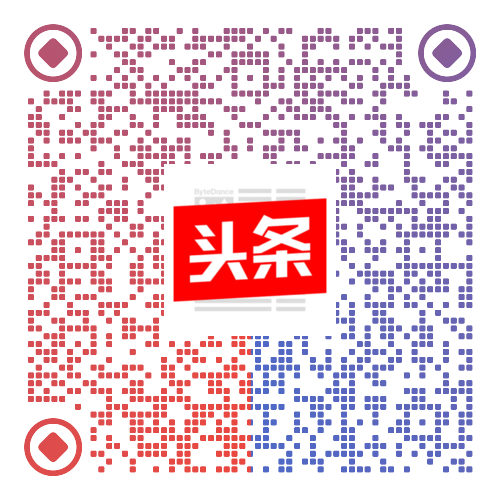墙角一株梅
趁着周末晴好天气,我把积攒了一个星期的外衣洗了,在阳台晾晒时,一不留神,晾衣架打了个滑,从手上蹦跳了两下,钻入阳台下的灌木丛里了。把衣服晾好后,准备下楼去找衣架。路过单元门楼西北角的背阴处时,不想与墙角处的一株腊梅撞了个满怀。那株梅,是土地润化自然而生的,还是经人随手栽下的,不得而知。弯下腰去仔细端详这株梅,树干有些纤细,不过二指宽,歪斜着,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,才从墙根与碎石的压迫里挣脱出半个身子来。枝桠也生得有些疏落,不像阳光下的其他树木花草,张牙舞爪地,肆意蓬勃生长着。它只是瘦棱棱地、默然地伫立着,毫无旁逸斜出的张扬与凌厉,像一位孤傲而沧桑的诗人,苦苦思索着心领神会却笔下不得的千年佳句。
也许是有了找衣架的相遇,我对这株墙角腊梅的关注无意中多了些。特别是小寒过后,空气中已经有了飘雪的气息。小区里其他树木早已刷上了白石灰,整装待发,抵御着即将到来的严寒。而这株腊梅单衣薄衫的,好像谁也没注意到它的存在。
那天周末下楼,带着儿子去小广场玩,我又鬼使神差地转到了西北角,就想看看这株饮风食雨的腊梅,是否已经枯萎了。刚走到背阴的墙角,一点极淡的花香、似有若无般钻进了鼻腔。我不由得驻足,抬眼望去,我看见了花。不是繁盛如云锦那般,更无铺天盖地的声势。只是在那最嶙峋的、我以为早已枯死的枝头上,冒着三五朵。花瓣是蜡黄的、单薄的,像是穿了一件紧身衣,紧紧地把花蕊裹在里面,那几近透明的黄色里,又隐约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、没有血色的浅白。它们不像春夏之交的花儿,在绿叶的衬托下,犹抱琵琶半遮面,欲说还休。它们就突兀地站立枝头,迎寒风、饮冰雪,孤傲不群。用手一摸,彻骨的寒气传遍全身。可它们开得又是那样的安静,那样的收敛,仿佛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,行人走路带过的风声,都会惊散了它们。可那缕幽香,你是抵挡不住的。屏住呼吸,定住心神,它从冷空气中剥离出来——细丝丝的,凉沁沁的,甚至有些霸道地,直钻入你的鼻腔。而就在这一瞬间,这几天来的不悦与烦躁,仿佛都从脑海中纷纷溃败逃散,自行给它让了位。那种独特的香气不由得让你,脑门一紧、心头一颤。
墙角的这株梅,它选择在这万物最为萧条的时节,在这阳光最少眷顾的角落,悄然完成自己生命里的盛宴。不向繁华献媚,不向喧哗靠拢。春暖花开的盛宴,群芳争艳的舞台,与它全然无关。它傲立的姿态,将彻骨的寒气淬炼成一缕幽香,这是一种何等倔强而又安分的“活法”!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嫉妒。它不争,并非无力,而是将这意志,全然倾注于对自我本真的成全。它的绽放,是给自己看的,给这面墙看的,给在阴暗里寻找阳光的探索者看的。
这墙角与梅,便构成了一幅完整的、自我完足的世界。墙的灰暗,点亮了梅的皎洁;梅的幽独,又成就了墙的寂寥。它们彼此需要,又彼此独立,在无人注目的角落,达成了一种静默的、永恒的默契。“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”。诗人王安石是不是也如我一样,在一个寒冬的午后,就在墙角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了一株凌寒独自开的梅?又或许是这墙角的梅本就是循着幽香穿越而来的?
自此,每当我意乱神疲之时,便想起那西北墙角里,几朵细黄的梅花。物竞天择,它就在那里,不挪不移,不媚不争,只是本本分分地做一株梅。在属于自己的时节,属于自己的角落,活出属于自己的,那一点凛冽的、皎洁的、透骨的清香。
世间繁华,梅有傲骨,人若真正明白这一点,也便足够了。
(肖日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