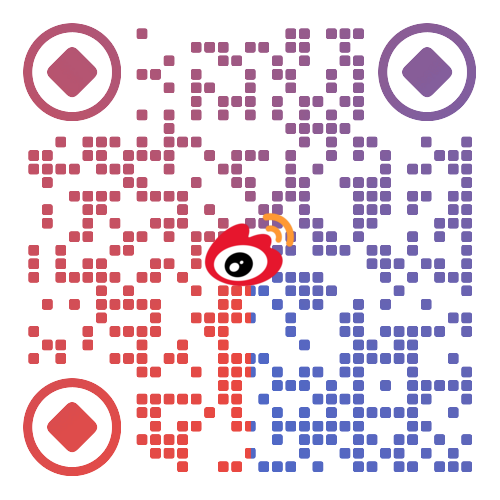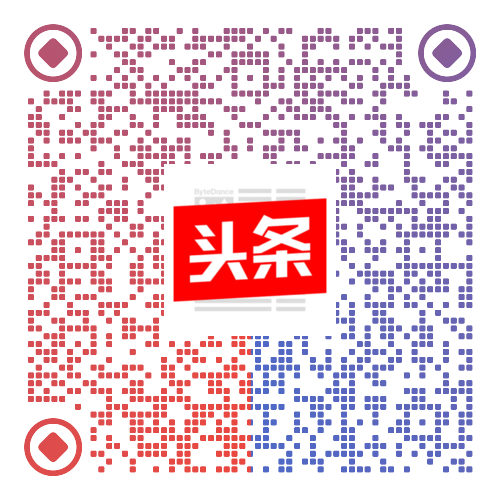叔叔的拿手杀猪菜
腊月清晨的霜还未化尽,院里的鼎沸人声却先一步热了起来。待到那头膘肥体壮的年猪在众人的协作下处置妥当,满院的喧腾宛如退潮般缓缓落下。白茫茫的烫猪水汽与稻草灰烬的余烟,在清冽的空气里盘旋。有人将一副最新鲜的肝肚下水,送进了灶房。
我的叔叔已从院中离开。不知何时,他退进了灶房,就着窗光,在那块厚重的枣木案板前站定,用一块旧布一遍遍擦拭着那双宽厚的手掌。他背对着院子里渐散的烟气与闲谈,独自沉浸到另一场更专注、更沉默的仪式里。
灶房里,光线微暗,却另有一番乾坤。粗木案板上,躺着一副刚从膛中取出、犹带体温的新鲜猪肝,恰似一方浸润过的深红玛瑙。他不急着动刀,而是先从墙上的皮鞘里抽出一把窄长的刀,在门口的光里,对着磨刀石“嚯嚯”地荡了几下。
那声音沉稳而规律,恍若在为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划定一个庄重的界限。然后,他左手微拢,稳住猪肝,右手刀锋贴着肝面轻快划过。刀锋顺着纹理游走,将肝切成一片片匀薄的柳叶,在空中划过,整齐地码入碗中。整个过程没有一丝犹豫,只有刀锋与案板接触时规律而轻盈的“咄咄”声。
手上动作刚停,他侧身看了一眼灶膛。硬柴噼啪作响,吐出金红的火舌。他偏头看一眼火色,待到铁锅烧得青烟微起,才将一勺金黄的菜籽油滑入。“滋啦”一声,几点花椒炸开,奇异的香气猛地爆出。
顷刻间,腌制好的肝尖被倒入滚油,白色的水汽混着锅气轰然蒸腾。叔叔单手握住锅柄,手腕一抖,那片片深红瞬时在锅中翻飞起来,像被风卷起的秋叶。他另一只手点入酱油、盐粒,撒上一把自家晒得焦红的干辣椒圈。火焰窜起,舔过锅边。不过几十秒,一道油亮酱红、点缀着焦褐椒段的爆炒肝尖,旋即离火入盘,热气奔腾。
这盘肝尖,将被端出去,置于院中已摆开的、盛满酸菜白肉、血肠与各色年菜的席面中央。“你奶奶在世时,总说‘热肝冷肺’,离火的肝尖,耽搁一秒,嫩气就少一分。”叔叔将盘子递过来,略停了一停,方开口道,声音平静。那一刻我明白了,他守护的不仅是一道菜的火候,更是一条穿过时光、来自祖母的味觉训诫。
当这盘肝尖被置于堂屋八仙桌的中央时,所有的谈笑有了片刻的停顿。一双双筷子伸过来,夹起那油润发亮的薄片。堂弟一口咬下,眼睛立刻眯成了缝:“就是这个脆嫩劲儿!”父亲抿一口酒,再吃一筷子,并不说话,只那舒展的眉心和一声悠长的呼气,已是无上的赞许。我尝了一片,肝尖外层带着锅气的微焦香脆,内里却是难以置信的滑嫩,姜与酒的香气去尽了所有腥气,只余下醇厚的鲜甜,最后是干辣椒那一点恰到好处、令人额头微微冒汗的后劲。
就在这满桌的咀嚼声与满足的叹息里,叔叔背过身去,就着水缸里的清水,再次慢慢地擦洗起他那双宽厚的手掌。水流声里,满屋的喧闹仿佛都成了他的背景。至此,我方真正读懂,叔叔的“拿手”,从来不是秘而不宣的诀窍。
他是将一年的风霜、对家人的惦念,还有那份沉默的担当,都当作最珍贵的调料,细细烹进了这道菜里。年味,在这一刻不再抽象,它化作了舌尖上这片滚烫的嫩滑,化作了烟火气中,深植于家族记忆里踏实无比的滋味。